播客:“互联网鸡肋” 的生与死
日期:2025-07-31 16:29:20 / 人气: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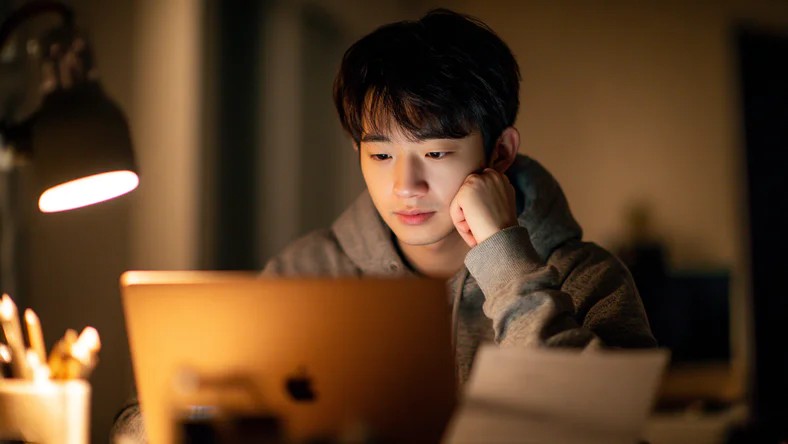
最近,播客圈经历了一次 “小地震”:头部播客平台小宇宙的 COO 芒芒(陈临风)、内容总编 ouli(欧里)、商业市场负责人小福均已离职。这三位分别掌管运营、内容、商业化三个重要业务板块的核心人员变动,无疑会对小宇宙乃至整个播客行业的走向产生影响。
小宇宙诞生于中文播客数量突破至 1 万档的那一年,可谓 “含着金汤匙出生”。之后,荔枝、蜻蜓 FM 等音频平台,以及百度、快手等互联网大厂纷纷推出播客 APP,试图抢占风口,但最终只有小宇宙经受住了市场考验,实现了最好的用户留存。然而,高涨的播客数量和可观的用户数据,却没能推动播客从 “元年” 迈向新的阶段。月活用户长期徘徊在百万的小宇宙,始终难以实现规模突破。大部分创作者仍在 “用爱发电”,无法全职投入内容创作,商业转化成为业内公认的阿喀琉斯之踵。
即便如此,不少公司仍前仆后继地布局播客行业,试图从中 “掘金”。前不久,腾讯音乐收购了播客行业另一大头部平台喜马拉雅,B 站也宣布大力推动 “视频播客计划”。更早之前,豆瓣、小红书等平台也已有所行动。这些频繁动作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源于局中人的 “不甘心”:大洋彼岸播客行业飙升的经济规模令人心动,而播客受众又多为黏度极高的高净值用户,放弃总觉得可惜。
在中文播客的商业模式还在原地打转时,AI 播客和视频播客作为 “搅局者” 试图探清行业前路。谁能率先破局解决难题,谁就能先发制人占据市场先机。只是,没人知道这盘中羹会不会变成手中沙,毕竟,折戟沉沙的过往还历历在目。
一、看似蓝海:播客的吸引力与潜在危机
行业报告上的亮眼数据,对入局者有着绝对的吸引力。在日渐下沉的分众化时代,播客的受众群明显有些特殊。据益普索的《2024 年播客行业报告》,18~40 岁听众占比 78.7%,为核心年龄段,其中本科及以上占比 81.3%,且播客收听人群以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占比超过 6 成。
这些高学历、高资产、身处一线城市的高净值用户,往往具有较高的购买力,尤其是黏性高、活跃的用户能将流量价值发挥到最大。正因如此,在消费层面,播客听众的消费意愿远超其他产品,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度。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购买付费播客节目的用户占比达 45.9%,其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听众付费意愿更高。听众对广告的接受度最高达 63.6%,退出率最低达 1.9%,51% 的听众在一年内有过播客消费,35.4% 的听众有过重复消费。
消费意愿与复购率都验证了播客的商业价值,自然吸引了不少品牌的商业投放。而播客大多为深度的 UGC 内容,能够进行长效的理念渗透,建立用户对品牌的深度信任,形成深度品牌资产。这使得品牌在进行传统意义上定制播客合作的同时,也在进行 DTC 模式的创新。比如,奢侈品 GIADA 邀请鲁豫担任支持人,创立《岩中花述》播客,邀请诸多女性榜样进行对话访谈,构建自己坚韧优雅的理念;理财产品有知有行创立《知行小酒馆》,长期聚焦于用户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投资场景问题,自然而然建立用户对有知有行 APP 的信任。
据《播客志》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 年 10 月,超过 120 个品牌自制或委托机构在 2024 年更新品牌播客。超过 180 个品牌进行过播客广告投放,较 2023 年增长 50%。
无论是用户心智还是品牌信任,都是其他产品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尤其是海外播客近年来令人振奋的行业规模,更是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自《Serial》下载量破亿、获得皮博迪奖之后,播客这个小众媒介开始走向大众化。先是 Gimlet Media、Panoply 等新兴播客公司获得千万美元级别融资,再是巨头大步入局。2019 年,Spotify 花了 4 亿美元连续收购 Gimlet、Anchor 和 Parcast,翌年,亚马逊以 3 亿美元收购 Wondery。《The Joe Rogan Experience》更是将播客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大科技公司把播客作为内容战略的核心投入,资本不断涌入,YouTube 宣布平台上播客内容月活超 10 亿,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巨头。前不久的金球奖,更是宣布将从 2026 年开始设立最佳播客奖项,这意味着播客获得了主流认可,成为重要的内容媒介。
美国播客行业的高歌猛进给国内市场规划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调研报告里中文播客的市场数据又足够耀眼。只是,在不同语境之下,难以突破的商业模式,让中文播客行业总是看上去很美。现实是,入局者以为自己登上的是蓝海上皇家加勒比巨轮的头等舱,实际上不过是红海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叶扁舟。
二、商业孤岛:播客面临的生存困境
4 月份,头部播客《不合时宜》因为欠薪实习生事件,将中文播客的商业困境摆到了台面上。在回应中,《不合时宜》透露了自己近一年的商单情况:2024 年 3 月~11 月期间,仅有一单广告合作,而类似于付费会员的 “不合时宜全球成长计划” 是其 2024 年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部分收入大约在 19 万元,扣除网站技术开发成本、设计费用、Stripe 服务手续费、剪辑费、人力成本和税费之后,净收入约为 13 万元。
可即便多来几个商单也杯水车薪。作为业内头部的播客,《不合时宜》在小宇宙的口播和定制广告定价分别为 38889 和 133333,这个报价远低于网红博主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的商单报价。更何况,网红博主的更新频率更高,而《不合时宜》有时连周更都不能保证。
JustPod 发布的《2024 年中文播客新观察》曾提到,一档完整播客节目的制作至少包含策划、录制、剪辑、发布以及宣推等环节,2024 年,中文播客创作者平均每期节目的净工作时长达 12.9 小时,其中剪辑平均耗时 4.5 小时。
“高成本低回报” 的生存环境很难让创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内容创作中去,更多是当作爱好来维持。据统计,目前近八成中文播客创作者兼职创作节目,全职创作者仅占两成,62.9% 是非全职,且无全职打算。而当下 84.3% 的创作者能至少每月更新一期节目,44.3% 的创作者能保持每周更新的频率。
并不健康的创作者生态进一步加剧了头尾主播的生存落差。行业内部人士大云(化名)告诉毒眸,现在头部和中部的播客商业投放情况比较好,有时会接到大品牌的集中投放,但并不如外界想象得那么好。而且现在播客起号没有那么容易了,如果在其他平台有一定粉丝基础的话,会相对容易些,“纯素人做播客太难了。” 据 JustPod 统计,创作者画像中仅有 7.1% 的创作者制作经验不足 1 年。
恶性循环发生的根源在于商业模式始终无法寻找到有创造性的突破口。目前来说,播客的商业化主要有四种模式:口播贴片、定制播客、听众打赏和付费内容。四种模式中,目前接受度更高的还是口播贴片,只用在节目过程中进行简单的介绍,占比为 72.7%,而定制播客和付费内容都是基于内容出发的节目制作,制作周期会更长。
这种选择下,播客 “慢媒介” 的特性与品牌追求即时转化的需求形成了根本性矛盾。播客是长线的深度音频内容,无法快速地提供短期转化,或者帮助品牌打造出声量,与追求高频曝光的短视频媒介逻辑相悖,对于追求密集曝光的品牌而言并不具有性价比,只有已经成熟的品牌会希望借此进行品牌理念的深化。
品牌客户不稳定,也让不少创作者无法依靠播客实现稳定的收入。2024 年 CPA 的创作者调研显示,58.1% 的播客创作者接受过商单咨询,55.2% 的播客创作者接到过商单,平均一年接 4.5 单,平均第 21~30 期开始有商单。
在大云看来,当下创作者做播客不能完全依赖于商业投放,可能更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粉丝社群,按社群的逻辑去做更多的事。“我觉得如果想靠播客赚钱的话,只做播客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找一些‘播客 +’的形式,比如,很多主播是用播客给自己的主业带量,现在很多心理咨询师开始做播客,其实是做自己的咨询品牌,播客作为中间的桥梁,去赚那个‘+’的行业的钱。”
播客面临的困境跟脱口秀行业有些相似,即如何将小众文化转化为大众消费品。不同的是,脱口秀作为文化内容可以借助载体进行传播,用线上反哺线下,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但播客本身就是媒介载体,缺乏其他实体产业的承载,为其转型设置了很多障碍。
三、鲶鱼来了:AI 与视频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AI 之下,无人幸免,播客自然也不例外。2023 年,Google 推出 AI 应用 NotebookLM,之后上线 AI 播客功能,即用户上传文档、视频、音频等文件,NotebookLM 就可以将内容转换成一段两人对谈播客。今年 6 月,字节跳动的豆包也上线了 AI 播客功能,其流畅性与自然度更进一步。
眼看着创作者们还没尝到播客行业的甜头,失业的苦头就先出现了。不过,AI 的高效性很难不令创作者心动,制作周期和精力成本都在推着创作者们半推半就地与 AI 工具达成和解。据 JustPod,48.6% 的创作者表示曾经使用过 AI 工具辅助播客创作,42.9% 的表示虽然没用过,但是想尝试。
不过在小宇宙 CEO Kyth 看来,AI 不可取代主播,主播仍是播客的核心资产,“主播永远不可替代的部分,在于他是一个真人,他的经历、他的情感是真的,他的脆弱、他的鲁莽、他的缺点也是真的,我是在听一个人向我袒露他自己,这是最打动人的、最珍贵的东西。”
在 AI 会不会砸了主播饭碗的讨论还没结束时,视频播客又悄然来临。美国视频播客《The Joe Rogan Experience》与特朗普、马斯克等人的对谈,在 YouTube 上有着千万播放量,即便是 3 个小时的内容,观众也甘之如饴。海外的视频播客越来越多,苹果播客排名前十的播客中,五档节目都有专门录制视频版;Spotify 排名前十的播客中,八档节目会专门录制视频版。
国内平台很快看到了苗头,纷纷试水。B 站推出 “视频播客扶持计划”,并推出了自制播客《一麦三连》;喜马拉雅试水站内首档视频播客《行走的思考》;抖音精选与 JustPod 合作推出 “精选奇遇记” 播客。
融合性发展并非没有道理,视频化播客的优势在于,视频的商业化模式已经探索出来了,按照视频的变现路径可以进行有效转化,保证内容的破圈输出。《名利场》曾提到,多年来,播客受众忠诚,市场小众,难以规模化,但随着视频的加入,尤其是 YouTube 的算法让播客的传播速度飞快。
据钛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B 站视频播客 “在运营、产品完全没介入的情况下”,受众已经超过了 4000 万,用户观看时长从 69 亿分钟增长至 259 亿分钟,涨幅超过 270%。在短视频多年以来对用户的规训下,显然视频化内容更令观众易接受。
这种视频化的商业模式对创作者也是友好的,视频平台更大体量的流量扶持和打赏机制,能够让创作者收获切实的收益。据《Tech 星球》报道,《菠萝油子》2024 年节目的商单一半来自 B 站,一半来自喜马拉雅,没有一单来自于小宇宙。
不过,问题总是潜伏在水底,播客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融合性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行业的困境。视频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另一个媒介,势必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来重构叙事逻辑和精进剪辑技巧,所以这并非是简单的转化,而是彻底的转型。所以,可以看到,目前视频播客更多是已经商业化比较成功的头部播客在进行尝试。
无论是 AI 工具辅助还是视频化转型,都是工具层面的革新,播客行业想要实现真正的突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本身的媒介难题中去寻找应对之策,这需要跟大众的消费习惯和审美习惯作斗争,更需要针对播客形态构建出一套更为适配的商业模式。
摆脱 “拧巴”,是播客行业的当务之急,就像人生,终究是一个预期与能力之间不断匹配的过程。或许,不如承认播客本身的宿命就是圈地自萌呢?
作者:新航娱乐
新闻资讯 News
- 从反荷尔蒙爱情剧里,读懂即时零...01-30
- 英伟达“付费买盗版”训练AI:中...01-30
- 职场与人生的自洽:选对价值评判...01-30
- 烘焙赛道“无限战”:当商超成为...01-30

